难忘的“红色记忆”——读吴晓煜新著《煤矿的红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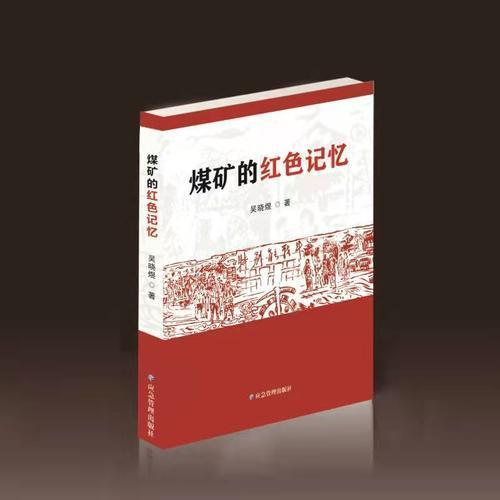
吴晓煜乃煤炭史志大家,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见到吴晓煜新著《煤矿的红色记忆》(应急管理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正是我们杂志社党支部全体党员刚刚从开滦寻访“特别能战斗”足迹归来之时。激动之余,我打开了吴晓煜的这本书,一口气读到了深夜。
正如吴晓煜在《前言》里所记录的那样,煤矿具有天然的革命基因。煤矿工人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依靠的重要力量,他们热爱党,革命意志坚定,勇于斗争,因而毛主席曾评价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煤矿是党最早开展革命运动的地方之一,党的许多领导人深入煤矿,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推动民族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党更加关心煤炭工业和煤矿工人,领导煤矿工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贡献、立新功,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中,继续战斗,实现煤矿工人的使命。可以说,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煤矿史,就是一部煤矿工人在党领导下的奋斗史、奉献史,这就是煤矿的红色记忆。
《煤矿的红色记忆》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时问世,是非常及时的,意义深远。此书共分为三部分:《革命先辈与煤矿》《红色往事与煤矿》和《文学作品与煤矿》。书中,吴晓煜满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对煤炭人的热爱之心,记录了革命先辈在煤矿留下的红色记忆,从孙中山、李大钊到毛泽东,从周恩来、朱德到彭德怀等。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对煤炭开发利用有着极其深刻的论断,“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之主要物,故其采取之目的,不徒纯为利益计,而在供给人类之用”。可谓高瞻远瞩,振聋发聩,和今天的煤炭人开采光明,奉献人类,一脉相承。孙中山深入山西阳泉等矿区考察煤炭储量,对于煤炭开采、利用、外运,以及如何增加矿工工资,降低煤价,便利人民等,做了统筹规划,描绘出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雏形。孙中山把煤炭和煤炭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概括为“不徒纯为利益计,而在供给人类之用”,这是孙中山与煤矿的红色记忆之核心。
在煤矿的红色记忆中,李大钊占有重要的位置。1922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一文,以煤炭为例揭开了矿工创造的煤炭剩余价值的本质。吴晓煜为李大钊对于矿工之厚爱叹为观止,写下悲壮诗句:“壮矣舍生向天歌,铁肩妙手今安在?”
吴晓煜特别介绍了曾经领导矿工站起来,不要做奴隶,要做天下的主人的领袖毛泽东。1921年7月党的一大结束后,毛泽东九次到安源煤矿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1922年2月,毛泽东组织安源煤矿工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1925年,毛泽东写下“他们特别能战斗”这一彪炳煤炭工业史册的最高褒扬;1936年在延安,他教导工作人员“应该向煤炭工人学习”。吴晓煜认为:“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煤矿工人的真诚爱戴与敬重,也是对延安军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教导。”
吴晓煜还记述了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井陉煤矿的感人细节,其中,周总理艰苦朴素的作风,给矿工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周总理顶着烈日到井陉一矿察看井架、井口、锅炉房、绞车房、洗煤厂、选煤楼等。午饭时,周总理仅吃了一小碗米饭和半块花卷。他说:“吃饭要讲实惠,不要搞花样子。要节约,不要弄鸡蛋,留下鸡蛋换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书中的《鲁迅与祖国的煤炭事业》一文令人印象深刻。人们都了解鲁迅是文学大师,很少有人知道鲁迅毕业于采矿专业。1898年,17岁的鲁迅摒弃科举仕途,考取江南水师学堂,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且是毕业时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人。1901年,鲁迅和他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当时的南京青龙山煤矿实习。他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叙述了当时煤矿的生产情况和恶劣的生产环境。1902年他到日本留学期间,也不忘关注煤矿,曾经把开平(今开滦)煤矿和日本煤矿相比较,曰:“顾其量,则甲东洋一切煤矿。”1903年,他在当时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概论》,引起强烈反响。1906年他与学友顾琅合著《中国矿产志》,是中国第一部矿产志。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在《序言》中指出:“顾、周两君学矿多年,颇有心得……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掠夺。”吴晓煜对鲁迅在其著作中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今日让与,明日特许……一任强梁者剖分,盖以赂鬻馈遗,若恐不尽”感动不已,呼吁今人学习鲁迅之精神。
另外,吴晓煜在《煤矿的红色记忆》中,记录了百年来矿山发生的一系列红色往事,如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安源煤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煤炭生产,20世纪30年代上海、延安演出的煤矿题材话剧《炭矿夫》,1937年举办的“煤矿救亡歌咏大会”,井陉矿工游击队,安源、淄博矿工挖地道开展游击战,以及煤矿工人创作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这些对于激励煤炭人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开采光明,奉献社会,意义深远。
书中,吴晓煜归纳总结了一大批革命老作家笔下的煤矿工人形象。对剧作家林艺创作的《矿灯》,吴晓煜说,这是他见到的中国第一部煤矿电影剧本。曹禺的话剧《雷雨》,不仅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雷雨》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遥相呼应,一个是反映农奴斗争,一个是写煤矿工人罢工。此外,吴晓煜还经多方考证,得出了“矿工鲁大海工作的煤矿在山东”的结论。
吴晓煜从巴金的长篇小说《雪》中,挖掘出作家对矿工斗争精神的歌颂。这部以矿工为主角的小说,最早在《大中国周报》上连载,当时取名《萌芽》。后来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煤》,再后来又改成了《雪》。先不说法国作家左拉的《萌芽》,“萌芽”是一种新生的力量,“煤”也是一种新生的力量,带有希望之光,吴晓煜认为“雪”象征着黑暗势力,很快便被小说中暗示的地底下的“火”所融化了。在作家的笔下,矿工象征着伟大的革命力量,预示着鲜红的太阳将照遍祖国大地。
读吴晓煜的《煤矿的红色记忆》,如同经受了一次洗礼,心灵受到震撼,对于从历史中汲取磅礴力量,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马茂洋 系《中国煤炭工业》杂志社副社长)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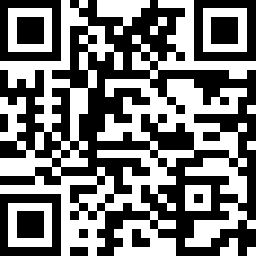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40102700086号
京公网安备1104010270008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