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方面的立法发生重大转变,要求合法的行为人在特定情景下承担危险责任——
风险社会,没有人能真正“独善其身”

前不久,四川省遂宁市首个高空坠物致人死亡案宣判。这一案件的判决结果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
事件是这样的。2016年11月11日,家住四川省遂宁市的李女士推着不满一岁的女儿经过油坊中街时,一只健身铁球从天而降。铁球砸到婴儿车中,女婴被砸身亡。事发后,当地公安部门介入调查,但未能找到抛物者。女婴父母将事发地整栋楼的住户全部起诉至法院。
2020年8月24日,船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因不能确定具体抛物者,包括底层门面经营者在内的整栋楼住户都有可能是加害人,除家中确无人居住的不用承担责任外,其余121户业主每户补偿原告3000元。据报道,已有住户提起上诉。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普通居民住宅越来越趋向高层,而高空抛物、坠物所带来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对于高空抛物,公民该如何防范,抛物者应承担哪些责任?无法确定抛物者的时候如何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如何避免全楼赔偿可能导致真正责任者“逍遥法外”而其他“可能加害人”均摊责任的不公平后果?就此,本报记者结合“四川遂宁高空抛物致人死亡第一案”,采访了相关法律专家和从业者。
故意抛物和无意坠物判罚标准有何不同?
高空坠物案件发生时,首先应判定其属于故意抛物还是无意坠物,这一点十分关键。近年来,随着法治进程不断加快,对故意抛物的判罚标准进一步完善。
“高空抛物案件一旦发生,不但将引发民事赔偿,还极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已对高空抛物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罪名认定作了指导。近期《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又释放出拟将高空抛物行为单独定罪的信号。”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法学专业老师李鹏辉介绍。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光华介绍,关于“高空抛物犯罪”,要结合抛物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情况及产生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其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定罪、准确量刑。其中,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而高空抛物的,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法律坚持从重惩治‘高空抛物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多次实施的,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陈光华说。关于“高空坠物犯罪”,陈光华介绍,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的,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具体侵权人难确定均摊赔偿是否合理?
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刘尉介绍“,四川遂宁高空抛物致人死亡第一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其一,本案加害人的可能范围;其二,承担责任的主体;其三,受害人的损失如何赔偿。
京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丁晶认为,本案之所以出现全楼业主须承担责任的情况,是因为无法找到具体的侵权行为人,与此同时又需要为受害人提供一定的法律救济。
据陈光华介绍,《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了抛掷坠落物品致害责任:“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是此案判决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确定不了具体的侵权人是谁时,对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依法可予以免责;其他“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则要共同给予补偿。至于“可能加害人”的范围,需要根据案发时受害人所处方位、抛掷物的种类、建筑物结构、损害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进行确定。
同时,陈光华指出,“可能加害人”承担的是一种代位补偿责任,若公安机关等查明真正侵权人时,可向具体侵权人进行追偿。
按照“同情弱者、损失分担”原则判决有无不妥之处?
具体到“四川遂宁高空抛物致人死亡第一案”的判决,很多专家认为有诸多可取之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侯佳儒认为,从保护受害者的角度出发,让所有可能实施加害行为的人对受害者的损失进行分担,在社会救助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为受害人提供必要的救济,体现了对业主和受害人利益的平衡,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促使因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而要承担补偿责任的建筑物使用人,积极提供线索,查找具体侵权人。此外,这样的判决能对民众起到警示作用,督促其采取积极措施预防损害的发生,有助于对公共安全的维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王乐兵认为,通过分散损失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对被侵权人进行救助,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救助色彩,也是现代风险社会实现风险分散和损失共担的有效机制,有利于构建安全和谐社会。
从理论上说,高空抛物案件受害人的损失可以通过伤害保险等得到补偿,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还不完善。陈光华认为,在找不到真正的侵权人时,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进行补偿,有利于合理分散损失,及时救济受害人。
同时,有专家指出此案判决中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孔梁成认为,判决书中部分地方使用“赔偿”一词不够严谨。在来源不明的高空抛物、坠物致害案件中“,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责任的原因并非因其实施了侵权行为,这种责任是一种“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丁晶也认为“,赔偿”表明了侵权行为人的过错、道德上的可非难性以及民法对其行为的否定,而“补偿”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否定评价含义。
其次,该案中只确认了可能性的有无,不区分可能性的大小,以户为单位划分责任和确定补偿范围的做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法学界有学者主张按照“可能加害”的概率分配责任,比如房屋的面积、窗户数量的差别等,都应考虑在内。
这种同情弱者、损失分担的判决原则,也让法学界的一些专家持明确反对意见。据李鹏辉介绍,这些学者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有三:一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找不到加害人的情况下选择由其他相关人员分担责任,这是对其他人员的不公平,也削弱了法律应有的威慑与惩戒作用;二是基于补偿责任的保障性,确定真正加害人似乎显得不必要,执法机关受此影响可能会淡化追求事实真相的意识,易诱发道德风险;三是相关人员服判息诉难度大,判决生效后实际履行率低,受害者因此难以得到充分救济。
由此,李鹏辉认为,正是因为相关规定存在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纠治高空抛物效果不佳,高空抛物依然屡禁不止。同时,高空抛物隐蔽性强、调查手段有限等诸多原因,导致很多时候无法查清真正的加害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空抛物案件的审理。
如何用法治手段精确防范“悬在头顶的痛”?
其实,司法实践中关于高空抛物的案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据李鹏辉介绍,早在20年前,重庆就出现了有代表性的“烟灰缸案”,受害人郝某凌晨在街上行走,被从天而降的一个硕大烟灰缸砸中,致使其头部受伤,郝某将当时临街高楼上的24户居民告上法庭,法院判决支持郝某由相关住户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随后,全国相继出现了济南“菜板案”、深圳“好莱居装饰材料案”等类似案例。
侯佳儒认为,高空抛物、坠物屡禁不止的背后,一方面体现了因建筑物区分所有受害人缺乏查找能力、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而同楼栋人“背锅”,早期只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公安机关推脱、不介入调查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部分民众素质不高、习惯不好的社会现实。
对此,我国首部《民法典》对“高空抛物”问题予以回应,对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规则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李鹏辉认为,《民法典》较《侵权责任法》有了一定的改进,既坚持优先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又赋予了其他人员追偿权,并对物业服务企业、公安等机关提出了相关职责要求。
“公安等机关利用其‘查人’‘找人’的优势和能力,更易发现真正的责任者,使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避免其他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责任,制裁真正侵权人的不法行为,预防高空抛物、坠物的发生。”王乐兵说。
此外,《民法典》中关于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也有利于促使建筑物管理人积极履行警示、防范等义务,预防损害的发生。比如,近日全国首个高空抛物监控系统在重庆投用,形成了“公安—社区—物管”三方联动机制,这将有助于解决高空抛物难监督、难取证、难问责等问题。
侯佳儒认为,在风险社会,侵权责任方面的立法发生重大转变,其立法目的不再强调对肇事行为的否定、道义谴责,而是从风险分配和损害填补的角度出发,要求合法的行为人在特定情景下承担危险责任。“以受害人作为参考,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则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向加害人求偿,但在加害人不明的情况下,保险合同、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公共基金等形式的公共赔偿制度,在实现分散和移转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方面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侯佳儒说。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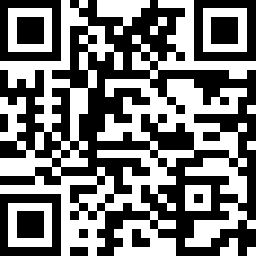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40102700086号
京公网安备11040102700086号
